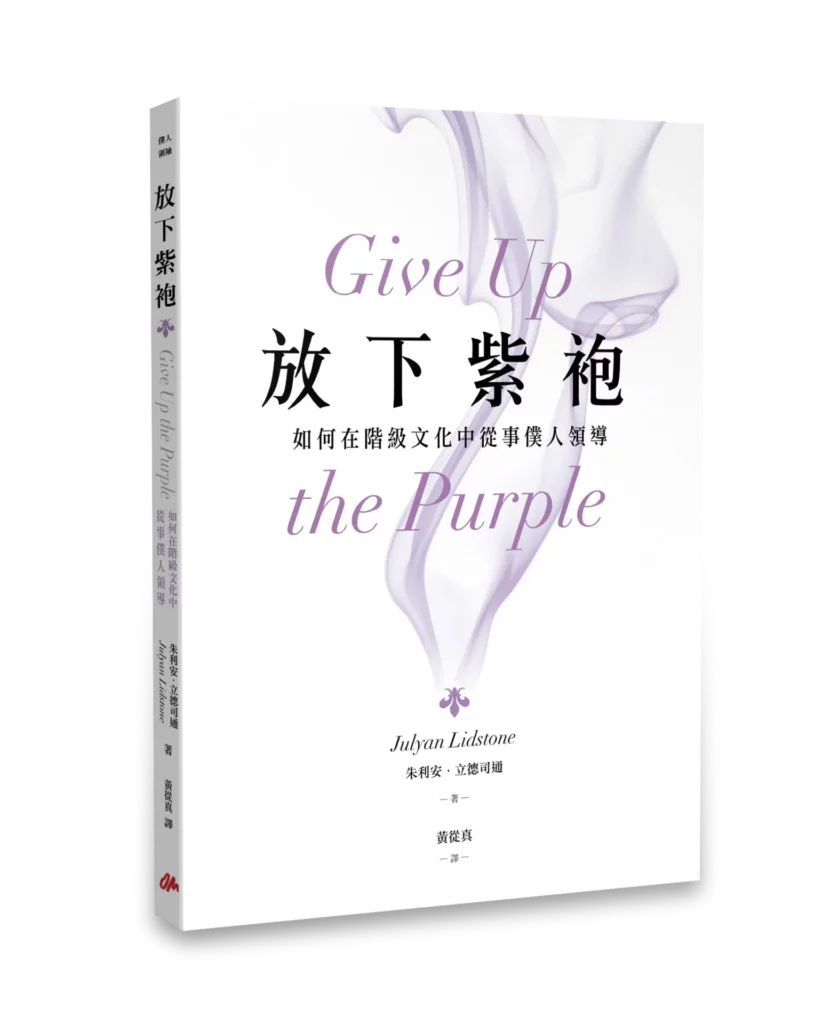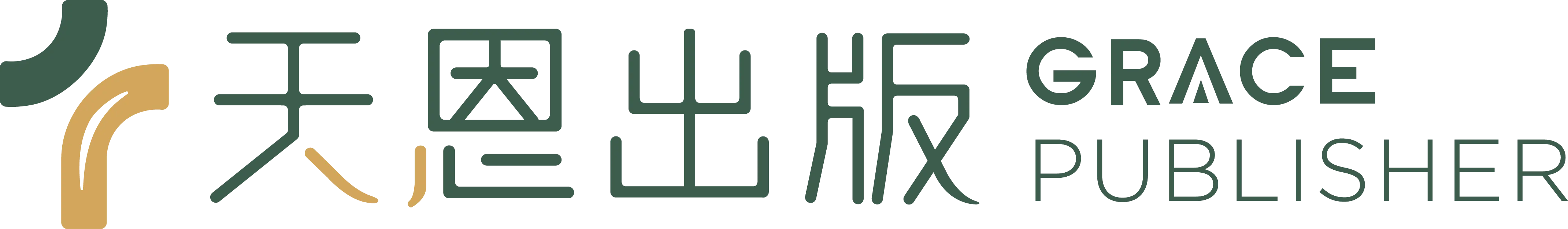- 登入
- 註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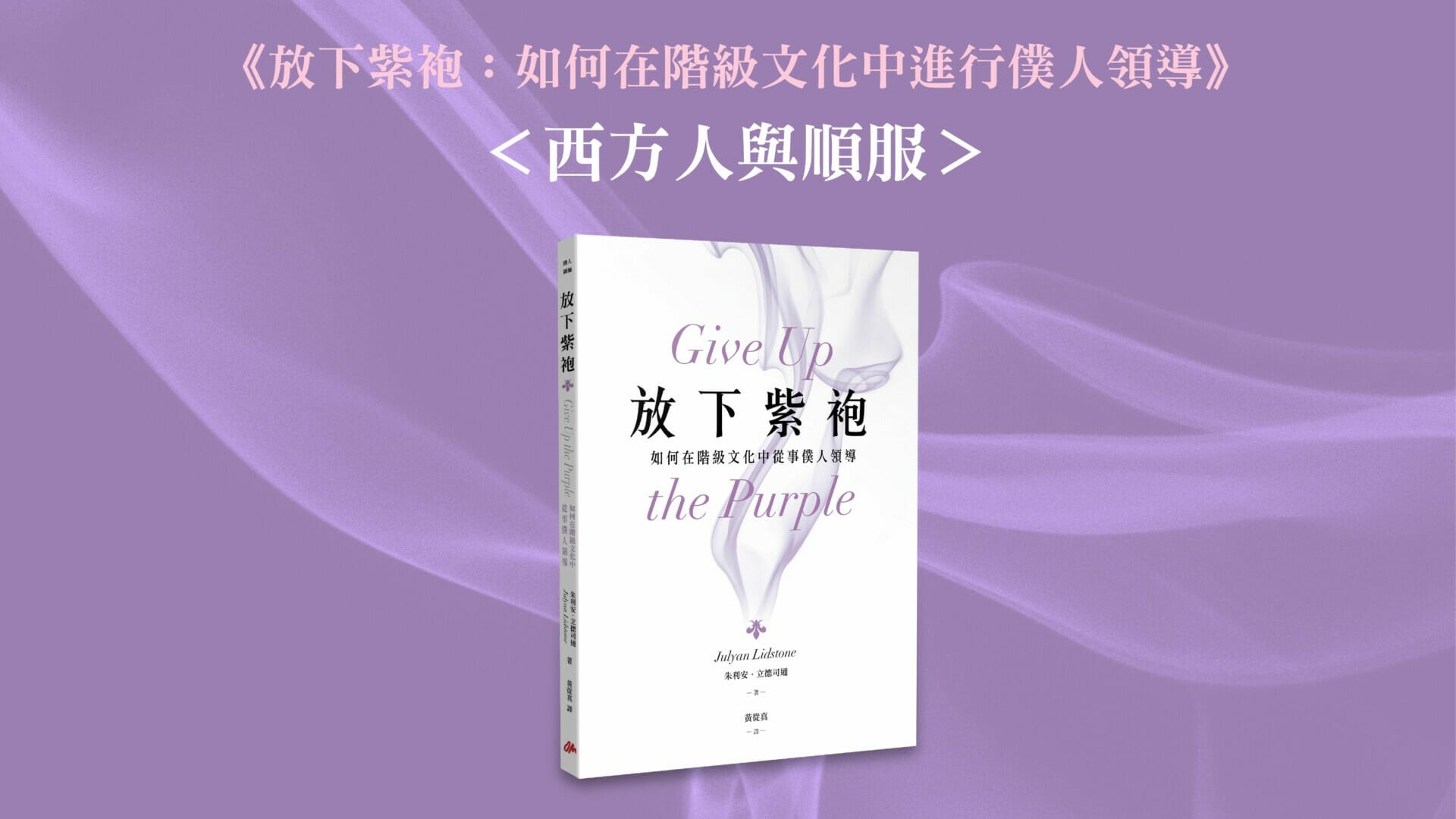
西方人與順服
後現代思維已教導我們要對一切權柄存疑,要看待權柄本身以及權柄裡面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腐敗,常常會被治理者強制使用,以遂行私自的目的。然而,我們對上帝權柄的順服,常常是要從我們順服人的權柄來表露的。順服是一種古老的屬靈操練,它教導我們即使不理解仍要信靠,也要求我們面對我們叛逆的本性在一個異文化的領導手下工作常常是一種奇妙的機會,可以學習毫不反抗或毫不要求解釋的順服,就是歡喜的獻上忠心的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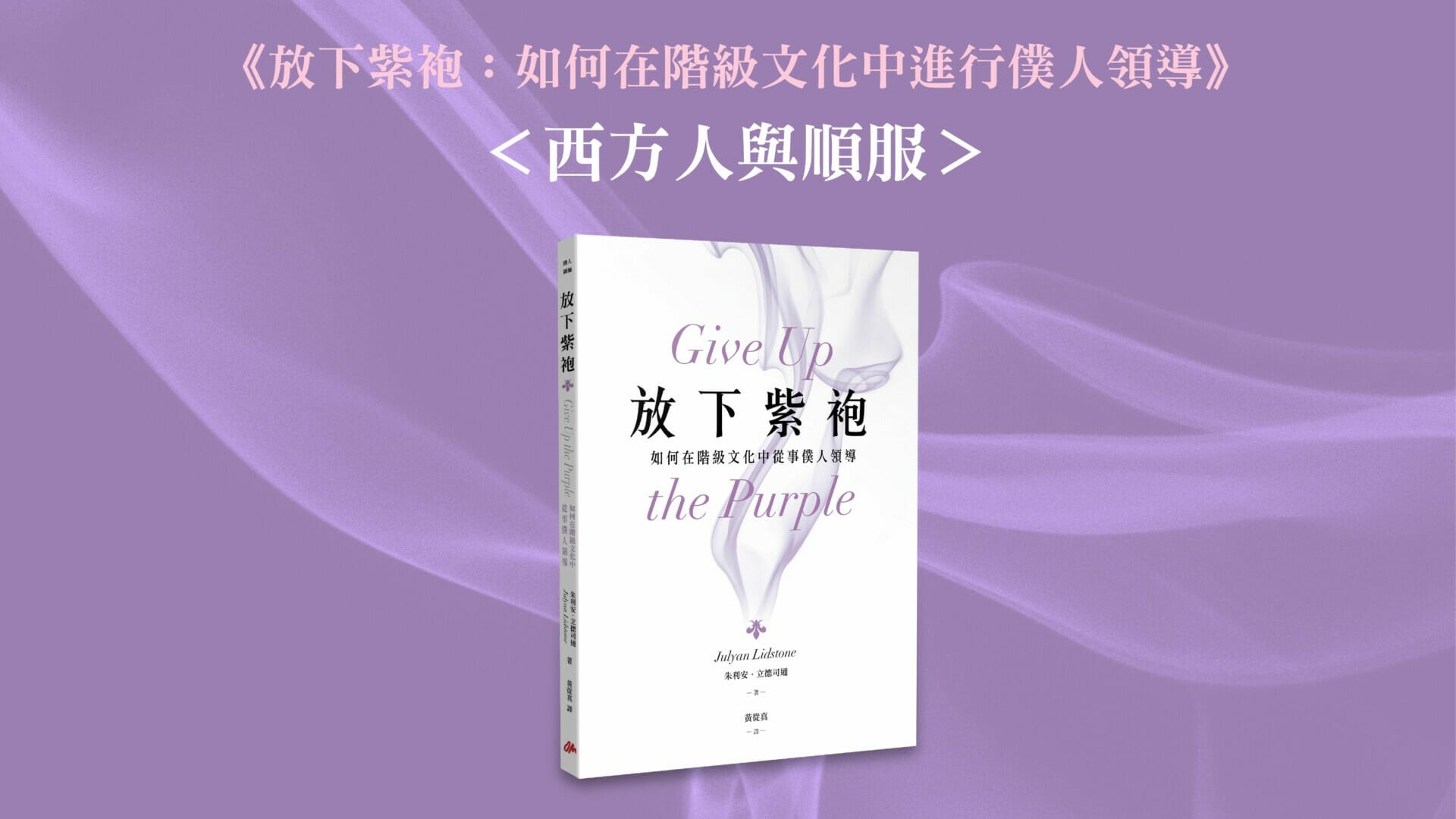
文 / 朱利安.立德司通,《放下紫袍》作者
後現代思維已教導我們要對一切權柄存疑,要看待權柄本身以及權柄裡面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腐敗,常常會被治理者強制使用,以遂行私自的目的。可悲的是,最近在教會濫用屬靈權柄以護短、替加害者說話的幾個例子,更增加了它的可疑性。
然而,我們對上帝權柄的順服,常常是要從我們順服人的權柄來表露的。順服是一種古老的屬靈操練,它教導我們即使不理解仍要信靠,也要求我們面對我們叛逆的本性。在一個異文化的領導手下工作常常是一種奇妙的機會,可以學習毫不反抗或毫不要求解釋的順服,就是歡喜的獻上忠心的服事。
1974年,我初次隨世界福音動員會去印度時才二十二歲,那是我從1960年代典型的學生反對運動者背景轉變後的一年。那時,印度剛在二十七年前從大英帝國獲得獨立。身為英國白人,我受到一些印度人以尊敬的眼神向我致意──他們對殖民時期政府的正面作為心存感激,也受到另一些印度人投以憎恨的眼神──他們不能忘懷鎮壓獨立運動所施予的不公與暴力。對我而言,若要採取一種未經思索的優越感或「我很有資格」的治理態度,那是輕而易舉的事。經過最初在達斯和拉吉所帶領的嚴格訓練之後,我被派往奧里薩邦(Orissa),在達南賈伊‧奈亞克(Dhananjaya Nayak)手下服事。雖然有幾次我很想批評他行事的方法,但我很快就發現我的責任是忠心的服事他,我的角色是要協助他把事做好。與其像其他組員一樣的鼓噪、抱怨他的工作倫理,我選擇挺他,然後必要時再私下提出討論。學習按著領導的吩咐,不去質疑或抱怨,那是我屬靈成長及跨文化訓練的重要關鍵,它教導了我尊重與順服的價值。
這種喜樂的順服不能與「在不公或濫權時卻仍緘默」混為一談。身為光明之子,我們蒙召就是要說真話,當我們看見權柄遭到誤用時,我們必須出聲關切。不過,當我們出聲時,仍然持續尊重在我們之上的權柄,不可趁此發怒、洩憤,而是要尋求什麼是對領導最好的做法,盡力協助他成功。同理,教會也要留心不要失去在社會中當先知發聲的角色。
在亞洲與非洲工作的西方人,被公開賦予榮耀和尊敬時常會覺得尷尬。在教會講台被推上高位、有人要幫你提手提箱、或在正式的演講中讚譽你的成就⋯⋯這些都讓西方人畏縮。我們西方人已經太習慣平等主義,崇尚非形式主義,以至於這類的舉止令我們覺得有點兒荒謬。有時候,西方的基督徒會藉著「拒受榮耀」的行動來反制這些;我們以為,這麼做可以為「僕人領導」立下榜樣──但這一切只會令人困惑,甚至反感。
有個故事說到,在西非一所神學院的某位英國籍院長,為了示範僕人領導,他開始做起園丁的工作,替神學院的花園除草。這使得神學院的其他員工大驚失色,他們來找他磋商,向他解釋這樣的做法使他們格外尷尬。一所令人看重的學院,它的院長竟做起園丁的工作,外面的人會恥笑說:院長無能,沒辦法叫員工盡忠職守。院長的做法,他們看在眼裡無法贊同,只覺怪異。院長或許有更好的方式來服事他們,是符合他們所期望的,並能謙遜地接受他們的文化。
那麼,耶穌又為什麼做起「替門徒洗腳」這麼令人驚訝的事呢?我們又當如何效法祂的榜樣呢?一部分的答案是:耶穌置身在同文化的圈子中,祂能夠準確地評估祂的行動能不能被接受,也知道它會帶來什麼影響。這個象徵的行動有深刻的影響力,因為它違反體制;按道理都是由奴僕替人洗腳。透過替門徒洗腳,耶穌既未否定祂的權柄,也未假裝祂是和他們同等的,因為祂在解釋這個行動時說了:「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約十三13)
三位一體的模式也挑戰了西方教會所允許的方式──以群體集思廣益來影響它的領導。雖然我們的確可從世俗界的作者如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和派翠克‧倫丘尼(Patrick Lencioni)的智慧汲取睿見,但更多時候,世上的成功是靠數字、預算和建物來定義的,而成長也是按機械化的項目來理解,以致幾乎沒什麼空間容讓聖靈工作。
當牧者看自己就如大公司的總裁,要帶領會友達成他個人的異象宣言,並從會友的奉承中找到自己的意義時,這種個人主義就不會允許各小組的領袖們去操練我們在新約聖經所看到的愛心,以及彼此順服了;反而更像是追逐聲譽為重的庇護者領導,不斷壯大自己的聲勢,假以時日後,志得意滿到以為自己可以超越一切的問責(不必向誰負責),結果,伴隨著醜聞和羞辱而跌下無可避免的懸崖。
(摘錄自《放下紫袍》〈第8章 蒙救贖的領導學〉,台灣OM世界福音動員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