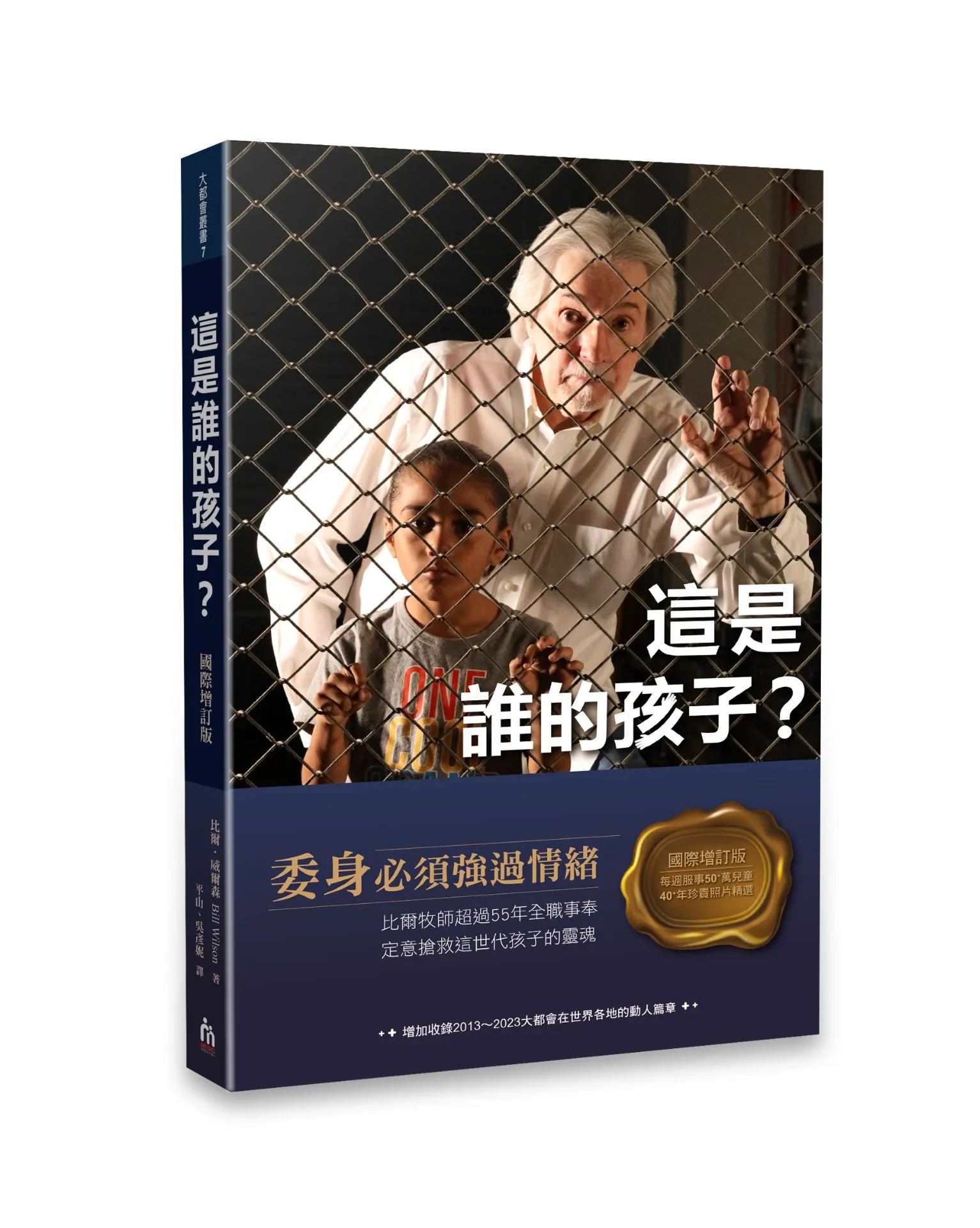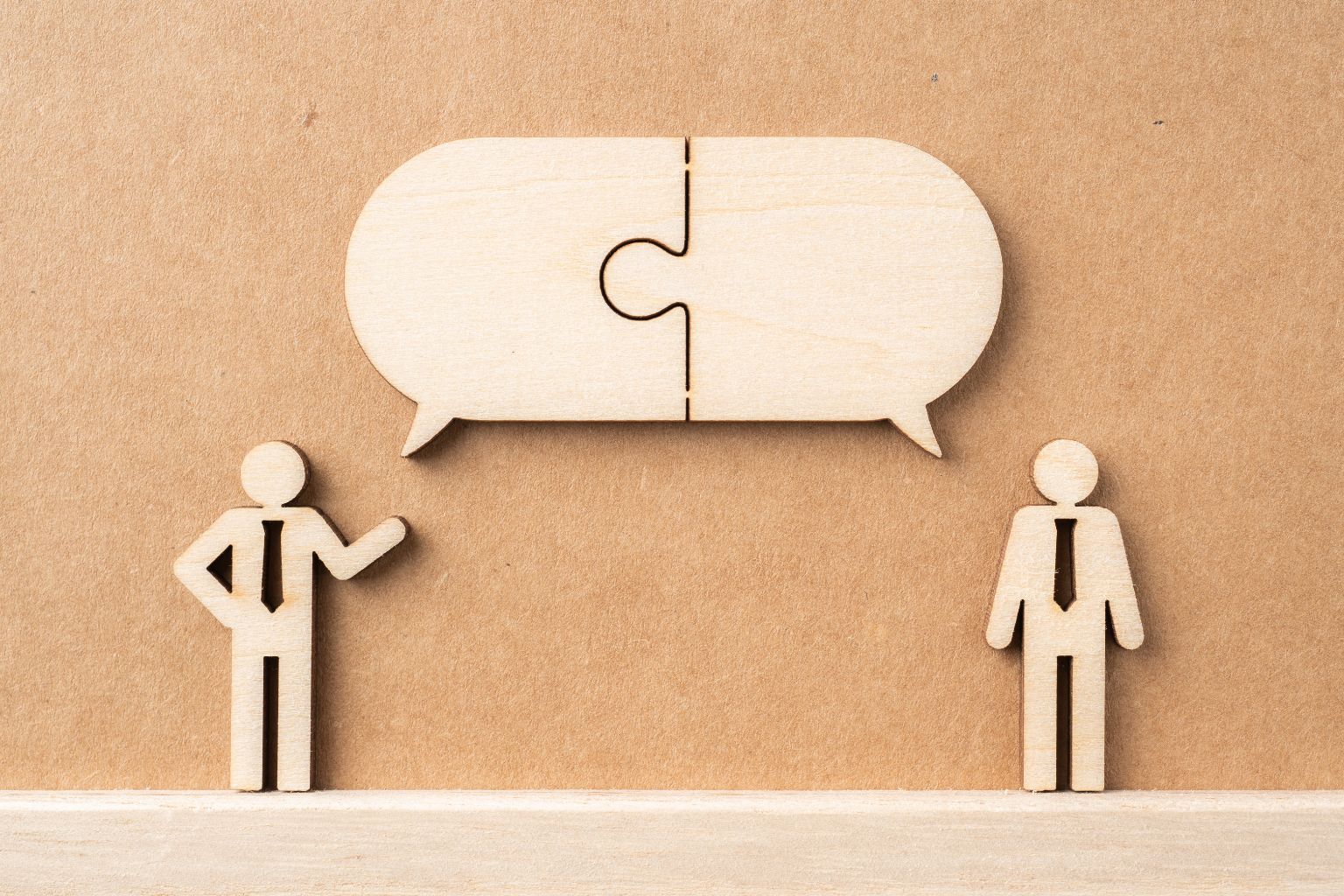耶穌,沒有人要我…如果祢要我,我在這裡

文/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這是誰的孩子》(國際增訂版)作者
耶穌,沒有人要我。但是如果你要我,我在這裡。
那年我十二歲,母親和我走在我們社區的街上,就在佛羅里達州的聖彼得堡,離公園大道的歡迎旅館很近,她在那裡當酒吧女侍。我們停下來,坐在混凝土排水溝上。她異常安靜,幾分鐘後,她起身說:「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你在這裡等著。」她在講什麼?不能再繼續下去什麼?
我確實照媽媽所說,坐在那裡等她回來。隔天我仍坐在那排水溝上,也在思索一些事情。我知道對爸媽來說,那段時間很困難。爸爸找到開巴士的工作,卻不夠養家。當時我十歲,姊姊大我八歲,她是我生命中惟一穩定的因素,她總是盡力鼓勵和保護我。我是個瘦小子,一直都是社區惡霸的箭靶。爸媽離婚後,爸爸得了肺結核,住進醫院。
媽媽,你要去哪裡?
我小時候從不覺得父母疼我,我媽為了撫慰不幸的生活,成了個酒鬼。她差不多每晚都會從酒吧帶不同的男人回家,這些人是我所見過最粗暴的人。夜復一夜,我都在咒罵、打架、飲酒狂歡聲中入睡。
有一晚鬧得實在太兇了,我找出一把槍,準備射殺我媽那晚的伴侶。
我坐在排水溝上的第二天,想到媽媽沒回家的那幾個夜晚,難道又發生了嗎?她應該很快就回來了吧。那三天,我不知道該向哪裡求助。姊姊結婚了,爸爸死了。如果我早學會怎麼禱告,我就會禱告,但宗教信仰在我們家毫無地位。我只能鼓起勇氣把滿眼眶的淚水往肚子裡吞。
媽媽沒回來。
一名住街尾的人注意到我那三天坐在同一個地方,他的名字是大衛.魯德尼。他走過來,我們開始聊,他問我能否帶些食物給我。他問我:「你還好嗎?」我回答:「應該吧。」
「你想不想去主日學夏令營?」他問。「那是什麼?」我回答。「你會喜歡的,很多你這年紀的孩子都會去。他們有壘球、游泳和很棒的聚會。」聚會?我心想:那是什麼?五個小時後,大衛付了那週的學費,把我和幾個青少年送上教會的福音車。

不再孤單
基本上我是個獨行俠,我不知道怎麼和人建立關係,另外也因為我那個糟透了的自我形象。我根本瘦的像根竹竿一樣,還有一副大暴牙,還有個變形的下巴,褲子也老是有破洞。
我不太跟別人來往,但是在週三晚上,我在營會中聽到一件全然改變了我生命的事。我第一次聽到耶穌怎樣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祂後來死裡復活,使我能在永恆中與祂同在。
我不記得營會講員和當天的講題,但那晚我走到前方,跪在講台左邊。我說:「耶穌,沒有人要我。但如果祢要我,我在這裡。求祢赦免我的罪,我把我的生命交給祢。」不知怎的,我知道從那晚起,我的未來不再一樣。
我回家的時候,大衛等著我。他聽說我在營會裡找到主了。「孩子,我希望你知道我們有多愛你。別擔心,不會有事的。」我從來沒聽過像那樣的話。
下個週末,我第一次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主領詩歌的人說:「讓我們翻到二百六十九頁,唱『活水泉源』。」我沒用詩歌本唱歌,我不曉得自己唱的和別人不一樣。有一位親切的老太太坐我後面,她傾身向前,摟著我的肩膀說:「我教你怎麼唱。」
教會的人對我很有耐心,我甚至搬進了大衛的教會裡住。教會的人真的關心我,讓我有歸屬感,而不是一個外來訪客。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影響誰
從我將生命獻給主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生命將更豐富多彩。我向一些小時候來上大都會主日學的人請益,幫我表達大都會做的事情的重要性。
伊賽亞.德魯里
「二○年代初在布魯克林的布朗斯維爾長大並不容易。每天當我走路上學的時候,總會看到有人在街角賣大麻和進行非法活動。每天我都會對自己說:『長大後我也得跟他們一樣』。我這麼說,是因為我沒有希望。我生在一個單親家庭,和媽媽及六個兄弟姊妹一起長大。當我大概兩、三歲時,我媽媽和一個酒鬼廝混。
三歲時,開始參加大都會兒童主日學,一個名叫普林絲的女士是我住的社區的巴士隊長,每週五她都會來敲門邀請我去主日學,她像我心目中一直想要的媽媽。十三歲時,普林絲問我是否願意成為她的幫手,我當然說好!
青少年時期,我經歷了很多事情。十四歲時喪父,初中被診斷出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和注意力缺失症。但是我告訴你,這沒有阻止我來上主日學。
你可能不知道你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有多大,你給的擁抱可能是他們那週惟一的擁抱。如果沒有大都會國際兒童事工,我不知道我今天會在哪裡。那是我的過去,但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說,我是祂的故事。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獲得了兒童教育學位,今天我是紐約布朗斯維爾的海洋山社區一所學校的副校長,我仍然在協助主日學的工作。」

我的心我們見證伊賽亞長大成為一個神的子民,因為他決定打破常規,抵制刻板印象,不成為統計數據。
大都會國際兒童事工持續增長。為了讓孩子願意來到耶穌面前,我們需要做更多。有些孩子的生命取決於此,他們仰賴我們和為他們所做的,去提供生命中的答案。
(本文摘自《這是誰的孩子》(國際增訂版))